重轻:Funes 在筹集什么?
真实世界悄悄凋敝,又生生不息
今天是连载的最后一期,前情提要。
微软模拟飞行游戏的最新版本,通过在线串流的方式给玩家提供极其逼真的飞机飞行和起降的窗外风景。游戏的开发者和奥地利的一家名为 Black Shark Al 的公司合作,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基于卫星俯拍整个地球表面的照片,生成了地面上全部的约 15 亿个建筑。
这显然又是数字孪生愿景下的一大创举,只是其中一个细节不太方便:这些建筑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当热心的玩家在游戏里飞到自己生活的小镇,发现自己熟识的街头巷尾,教堂和学校,没有一样是对的。它们不是门开错了方向,就是在没有窗户的墙面开出了落地窗。但另一方面,玩家似乎又觉得这只是自己的矫情--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整个世界看着都毫不违和,它清晰可辨,简直是将整个世界装进了小小的电脑屏幕,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尽管有这个小小的不便,从任何意义上讲,开飞机的仿真软件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完美的应用场景。毕竟用户正在享受驾驶的乐趣,而不是在考证自己呼啸而过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城镇、灯塔和桥梁是否是对真实世界忠实的描绘。
人类自古以来就在模仿,记录和展示自己不拥有,或不在场的事物。但在摄影术发明之前,模仿和记录的唯一做法就是制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这件事持续了几千年,是如此的不假思索。直到 20 世纪,这古老而永恒的行为发生了两次大飞跃,或者叫大后退。
第一次,是本雅明充分讨论过的摄影技术。摄影的发明,让复制这件事从无可避免的人工斧凿,变得完全机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伤感地追悼机械复制过程杀死的,蕴含于原始物中的“光韵”,即那种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它的,“独一无二的展现”。光韵衰竭了,因为大众有强烈的愿望想要接近那些美好事物,于是通过摄影掠夺其意义,剥掉它的独一无二和永久。一切山岭都在方块里,一切视野都在平面里。机械复制出来的酷似物,让人人可以贴近它,占有它。
第二次,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当下。微软模拟飞行的例子是一则完美的寓言:史无前例地,我们可以只要一个对象(或者整个世界)的印象,而甚至无需它或它的复制品。今日技术已经深入人意识的腹地,用不可阐释也无需阐释的神经网络把握了我们自身的感知,而非外部对象。这一次 sense making 的机器隆隆作响,摧毁的不是事物的光韵,而是事物。
在元宇宙的愿景实现之前,技术将把元宇宙内部万物的造价降到 0。看着像教堂的教堂,看着像庭院的庭院,一切似是而非的堆砌,如同指认人类认知局限的累累证供。我们还需要真实世界么?
如果人活着,就只是在与脑海中盘旋的印象周旋以攫取快乐和意义,那么这问题就很难回答。所幸并不是这样。飞行模拟对飞机进行的归纳和舍弃,是建立在其实现飞行员驾驶乐趣的前提上。这无限的麻烦就来自前提,来自视角,来自万千情感和迫切,万千尚未显露的谜面。当我们把一座塔摆在桌面,把一幅画虔敬地挂在家里墙上,我们就要面对这个事实:当前提暖昧不清,细节就不好舍弃。真实的份量就在于此。
真实世界的存在,没有单一的假设,也不挂载明确的意图。它诉说,但不说单一的故事;它显露,但不露出单一的秘密。它不嚎叫着让你注意一件重要的事,它只静静地存在,邀请你献上你的前提,你的视角。
本雅明哀悼的,是机械复制时代抛下的原真;而 Funes 建造的:是印象时代抛下的机械复制。所以 Funes 从来不是一个关于筹集廉价劳动力以生产那些定价势必归零的元宇宙资产的生意,它甚至没有在筹集模型。真实世界悄悄凋敝,又生生不息,只是某时某地有一栋房子,一个街角,让一个人忍不住走出家门去记录,因为他在意。
Funes 筹集的就只有这一样。前提。理由。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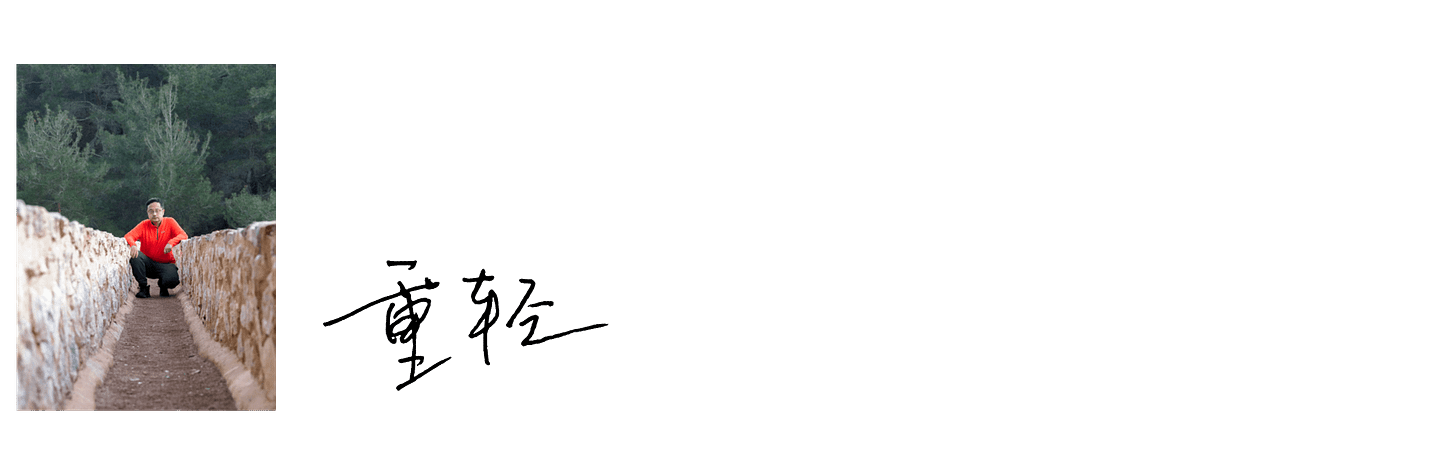

重轻的老听众了,从小宇宙的播客节目得知了这个项目过来的。
初步了解了一下这个项目,感觉跟我正在写的手机app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很高兴,这说明我们有类似的问题意识。
希望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能成为这个项目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
在意就是最大的初心:)